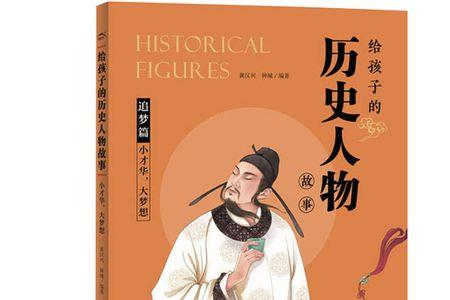“一个放羊的孩子被狼吃了。”
如果我们这样讲述,就是事儿。
“一个放羊的孩子因为再三说谎,以致呼救时无人相信,最终被狼吃了。”
这样讲,就是故事了。
事儿只是事儿,是发生过的经历,从叙事层面说,与我们说的“流水账”非常接近。而故事是经过讲述者的价值与情感过滤,重新建构出来的(所以严格地讲,故事就是故事,不存在“真实故事”,纵使故事会为我们带来真实的心理感受)。
我们需要具备同理心的天赋、年老的灵魂,并为刻意训练投入时间,才能把事儿讲成迷人的故事(关于如何从整体到细部搭建出动人的故事,我已经写过很多方法论与实例,就不再重复)。
但很遗憾,从审美上讲,故事未必比事儿高级。比如《局外人》就更像一连串发生的事儿,很难称得上是个故事,但不妨碍它是顶级的文学作品(当然完成这样的作品比写故事难太多)。
故事的整体搭建是明显包含因果的。想想“狼来了”的故事,因为孩子再三说谎,所以失信,被狼吃掉。
由于紧密的因果贯穿,编排缜密的故事看上去仍像是精美的提线木偶——哪怕我们技艺精湛,能让木偶做出与人类精度相同的动作,但那些拴在木偶上的尼龙细线仍会在灯下发出闪光,提醒着讲述者:这一切终究是刻意编排,所有因果也满含个人理解的局限。
另外,“狼来了”这个故事的根儿,是讲述者试图规劝孩子不要说谎——这多少怀有一点人类的自大(这是我对故事本身的一点反思)。
假如你和这个放羊的孩子一起长大,他住在你的隔壁,来你家吃过饭,替你出过头,也因为自己的面子做过带有英雄主义色彩却尴尬的事。13岁那年,某天你顶撞父母,被罚禁闭,没有和他一起出门。傍晚时分,你听说出事了,他死了。几年后,这件事变成了流传在周围村庄的育儿故事——一个男孩因为再三说谎被狼吃了。但你的心里只有疑惑:一个童年的伙伴、一个人,可以就这样死去吗,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你想写些什么,试图回忆和他相处过的细节。你很难搭建完整的逻辑,只有悲伤在文字间流淌。
相对故事,“事儿”是事情发生的本身,虽然有先后发生的时间顺序,但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因果。《局外人》中,默尔索杀的阿拉伯人与他没有任何关系,太阳烘烤出的汗水滴进他的眼球,接着,他扣下扳机。没人能总结出他具体的杀人动机,但我们会在其中感受到更微妙的情感与更高级的真实。
为了仇恨或是制度杀人,这样的故事是容易讲述的,但在迷茫中杀人才是更可能、更真实的。
励志和彼岸带有欺骗性,我们并不真切知道一件事的所有缘由,也不知所行的路通往哪里①。相比故事而言,“事儿”更贴近生命混沌茫然的状态,显得高级。
人类的信条是因果律,如果背离,我们将坠入黑暗的深渊。但在光的双缝干涉实验②中,是先果后因的(光在我们看它之前,已经知道了我们有没有看)。我无意让大家跳出因果,只是提供一点惊悚的事实,试图打开一种审美的可能。
当我们放下因果,进入时间本身,那些提着木偶的线在我们手上瘫软下去,木偶的肩膀却自发出现不易觉察的抖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