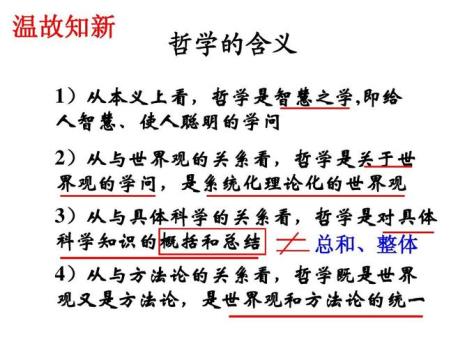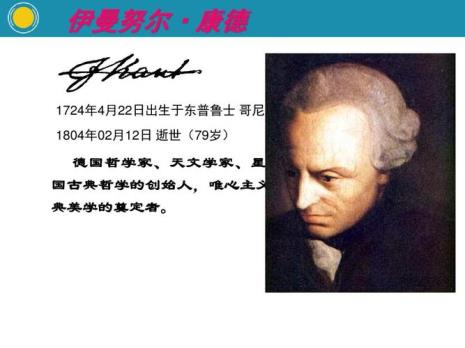17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一生未婚,他当然也有过结婚的念头,曾经看中两个女人,觉得有成为自己的老婆的资格。于是弄个表格,详列出结婚的利与弊。当他还在反复权衡是否该开口求爱之际,发现一位姑娘已经为他人披上嫁衣,另一位则早已远走他乡。
在康德在他的学说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,就是purpose和purposiveness的关系。purpose很简单,就是目的,德文原文是Zweck。所谓purposiveness是指目的性,某种目的所引发的价值或功利,德文原文叫Zweckmssigkeit。对此毛姆有非常通俗的解释:一个人盖房子,为的是出租,收取租金以改善生活,这就是他的“purpose”。而他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这一目的的价值与功利,即盖好房子之后是否能找到租户、应该收取多少房租才能在多少年内收回成本等等,即盖房子的“purposiveness”。
康德曾想过把结婚作为目的。但令他举棋不定的是这一目的是否值得,结婚之后的各种好处和坏处孰轻孰重。于是他索性做出了结论:人没有结婚的必要。既然他有这样的判断,让他这个哲学家当爱情专家也是勉为其难了。
没有目的性的目的是盲目的目的。这样看来,似乎purpose和purposiveness的关系很简单明了。但康德又说:purpose和purposiveness并不一定有关系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康德在他的一部重要著作《判断力批判》(Critique of Judgement)中有这样一句非常难懂的观点:“Aesthetic judgment is purposive without purpose”(美学判断具有目的性而无目的)。这是康德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。
康德认为,人有两种判断能力,一个是认知判断(cognitive judgment),另一个是美学判断(aesthetic judgment)。前者是客观的、唯物的,而后者是主观的、唯心的。所谓认知判断就我们运用经验与知识对物体客观的观察与认识。我们的头脑里已经有狗的概念:四条腿、毛茸茸、会摇尾巴、会叫。当我们见到这一个物体时,正好和我们头脑里概念对上号,于是我们就做出认知判断:这是一只狗。由于我们见到很多长得不一样的狗,于是就丰富了我们头脑里对狗的概念。所以,我们的认知判断既有purposiveness(因为我们有意用我们头脑里的概念去观察事物),又有purpose(因为我们成功地把我们的概念于见到的事物对上号)。
而美学判断(aesthetic judgment)则有所不同。当我们见到的物体无法与我们头脑里的概念完全吻合时,我们需要自己创造一个概念来指认它。这样创造就是美学判断。这个美学判断没有purpose,因为眼前的物体与我们原有的概念对不上号,但具有purposiveness,因为我们力图用新的概念来认知物体。
康德把这一超越局限的努力叫作“surplus intelligibility ”(额外的、或附加的认知),说白了就是想象力。想象力可以完全不拘泥于原本物体大致该有的概念,充分自由发挥,于是美学的快感就产生了。我们见到一轮落日,会想到残阳如血。见到一弯明月,便想到月光如水。此时我们已经不在乎太阳、月亮原本的概念是什么,也不在乎它们血和水有何关联。我们看一场惊心动魄的电影,与剧中的人物一起快乐或忧伤,早已忘记电影其实就是投射在银幕上的光影。
美学判断中的想象力不但需要认知判断所需要的经验与知识,还与每个人的情绪、兴趣、心情等个人因素有关。因此每个人的想象不尽相同。看到一幅画或听到一段音乐,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。艺术使人们产生多重的想象,正是其魅力所在。
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见到他的情人如见到女神,已经不把她视为万千女人中一员。但对于饿了三天的人来说,眼前的一只土豆要比一个女人更可爱。情人眼里出西施,饿汉眼里出土豆。康德对女人提不起美学兴趣,在他眼里,她们和土豆差不多,或许这就是大哲学家康德选择单身一辈子的原因吧!